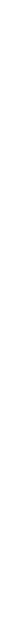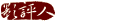|
|
| |
|
生者百岁,相去几何。欢乐苦短,忧愁实多。
何如尊酒,日往烟萝。花覆茅檐,疏雨相过。 倒酒既尽,杖藜行歌。孰不有古,南山峨峨。 |
||
|
|
| |
|
生者百岁,相去几何。欢乐苦短,忧愁实多。
何如尊酒,日往烟萝。花覆茅檐,疏雨相过。 倒酒既尽,杖藜行歌。孰不有古,南山峨峨。 |
||
|
|
| |
|
生者百岁,相去几何。欢乐苦短,忧愁实多。
何如尊酒,日往烟萝。花覆茅檐,疏雨相过。 倒酒既尽,杖藜行歌。孰不有古,南山峨峨。 |
||
|
|
| |
|
生者百岁,相去几何。欢乐苦短,忧愁实多。
何如尊酒,日往烟萝。花覆茅檐,疏雨相过。 倒酒既尽,杖藜行歌。孰不有古,南山峨峨。 |
||
|
|
| |
|
生者百岁,相去几何。欢乐苦短,忧愁实多。
何如尊酒,日往烟萝。花覆茅檐,疏雨相过。 倒酒既尽,杖藜行歌。孰不有古,南山峨峨。 |
||
|
|
| |
|
生者百岁,相去几何。欢乐苦短,忧愁实多。
何如尊酒,日往烟萝。花覆茅檐,疏雨相过。 倒酒既尽,杖藜行歌。孰不有古,南山峨峨。 |
||
GMT+8, 2024-6-27 03:55, Processed in 0.195547 second(s), 6 queries.
Powered by Discuz! 7.2
© 2001-2009 Comsenz Inc.